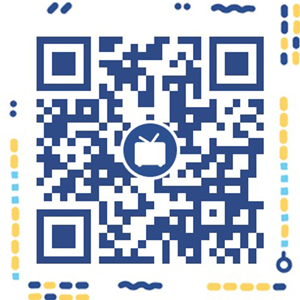作者:胡凯琳
西方歌剧洪流中,莫扎特是无法忽略的卓越人物,他的诸多歌剧在当今仍旧是各个歌剧舞台上久演不衰的经典,《唐·乔万尼》(Don Giovanni)就是其中一部。2017年12月13日以及14日,这部经典巨作再次在兰心大剧院拉开帷幕。本剧由上海青年歌剧团、日本昭和音乐大学的歌者们领衔主演,beat365英国官方网站合唱团与深圳交响乐团联袂演出。
《唐·乔万尼》又名《唐璜》,由莫扎特创作于1787年,剧目脚本为达·蓬特。同年10月于布拉格剧院进行首演,大获成功。该剧取材自西班牙民间传说《石客记》,讲述了贵族青年唐·乔万尼是一个好色之徒,他夜闯老骑士女儿安娜的闺房,将老骑士杀死,此后又对农妇采琳娜起了歹心,被唐璜遗弃的艾尔维拉与安娜一同揭穿了他的真面目,在众人的复仇以及老骑士石像的威慑下,唐璜坠入了阴曹地府。这部将生活和哲理糅合在一起,并且着重于人物的心理刻画的歌剧此次于沪上再度上演,是为作品诞辰230周年的纪念。
现代审美氤氲的对立世界
纵观整部剧,不难发现此次在舞美效果、道具布置、乐队配置等方面均有一些别出心裁的设计,这些特殊的设计很好地贴合了莫扎特的音乐,丰富了三维空间,在视听感官层面给予观众以全新体验,氤氲出现代审美下的对立世界。
剧目开场,幕帘拉开,目光所及处为一个四方舞台,四张桌,椅子若干把,四面摆放于桌内,一盆花团锦簇居中,这种简约而方整的道具摆放是古典主义喜好典雅并且对称的审美观的显现。舞台下方的乐池中,仅有弦乐组与打击乐的陈列(从左至右依次陈列:2只定音鼓,9把小提琴、2把大提琴、1把低音提琴以及3把中提琴),而管乐组则被陈列在舞台的两侧——舞台两侧设置了两层隔间,圆号、长笛等管乐居于其内。对于这种较为新颖的乐器设置,可以合理猜想是由于乐池的空间有限,但更可能的看法是,当代歌剧演出更为重视音响以及空间的合理设置,使其在原本剧场空间的局限中,产生集体融合又适度分离的音响感。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到此次演出,管弦乐队的规模并不大,这很好地还原了莫扎特时代、40人左右的规模。
在序曲音响的碰撞感中,观众瞬间陷入两个对立的世界里——阴郁不安的d小调,预示着石像客人后来的登场,然后是一个充满激情、无忧无虑的快速主题被奏出。在莫扎特的音乐当中,D大调与d小调从听感效果上就造成明亮与阴郁的对立感,另一方面从舞美效果来说,浓郁的克莱因蓝色静默,鲜艳地有些晃眼的紫红色氤氲成蓝色当中的一团,这种极强饱和度的灯光设置使舞台瞬间形成视觉上的对立,不仅很好地配合了音乐的分离感,更是渲染了主题的气氛——死亡与世俗、威严与淫乐、敬畏与嬉笑对立,体现了人性与神性的冲撞。
类似的灯光设计还体现在场景转换之间,舞台上的黑夜与白天,分别以白光及斑驳的深蓝色灯光来描述,照耀在纯白色的道具上显得格外生动。而歌剧中的某些剧情以及人物情绪(或者内心戏)有时候也由灯光颜色巧妙地传达给观众,印象比较深刻地是第一幕第二场时, 埃尔维拉出场,唱起咏叹调:“那个使我蒙羞的无情男人在何处?如果能在看到他,而他却不肯回到我身边,我一定要复仇!”这看起来充满怒气的情绪却隐没在白色灯光中,隐晦地表达出她虽然被唐·乔万尼遗弃,但其实心底还是强烈地被他吸引,身后围绕着一群衣着光鲜的男人们,被幽深的紫色覆盖,象征着性的复杂与诱惑,而她眼中却只有唐·乔万尼,反衬出埃尔维拉的专情。此刻,躲在暗处的唐·乔万尼被昏黄色灯光笼罩,看似不起眼的隐秘,但内心的欲望正在升腾。
唐·乔万尼的爱与悲
回到歌剧音乐以及唱段本身,柴可夫斯基曾评价其:“充满了高度的美,具有大量戏剧真实性的因素;曲调异常优美,和声配置特别丰富多彩而饶有兴味。”莫扎特的音乐勾勒出每一个生动的戏剧人物的形象与内心,其中作为整部剧的核心人物唐·乔万尼在此次歌剧演员的重新演绎当中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唐·乔万尼——这个来源于十五世纪的西班牙贵族,是某种价值观取向下的被批判者,引申到当代社会中作为一类人或者一段感情的“标签化”指向。但正是这样一个看似“作恶多端”的人物,却启发着后代许多诗人、作家、音乐家的艺术创作灵感:“从霍夫曼、克尔恺郭尔到肖伯纳和理查德·施特劳斯,唐·乔万尼成为一个理想人物。他是浮士德和超人,一个永恒女性的英俊骑士,甚至是生命力本身。”著名美国音乐学家约瑟夫·科尔曼(Joseph Kerman,1924- )如是道。这样一个形象较为鲜明、固定的人物,着实是歌剧演员的一大难题,在戏剧表演以及唱功都需要一定的功力。
第一幕第三场中,采琳娜与唐·乔万尼著名二重唱,从演员的表演中可以充分解读出两个人各自不同的内心活动。唐·乔万尼以无比甜蜜的旋律开始他的诱惑“让我们携手同行,我要向你求婚,那不远的地方就是我们的心房”,柔美婉转的旋律塑造出唐·乔万尼复杂而又充满魅力的个性形象,而采琳娜接着唱道“我愿意我又害怕,我心里真发慌”,她被诱惑却又心生恐惧和疑虑,演唱者犹豫的气息,很好地表现出了这一点。整个过程中,两人一来一往的乐句,宛如在博弈又似乎是追逐。其间唐·乔万尼的花言巧语,挑逗性地拉起采琳娜的手,肢体上的故意贴近,以及性感的眼神都无限地透露出致命的诱惑和危险。一个极致追求情欲、享乐生活的唐乔瓦尼在单纯天真的采琳娜的反衬下,展示在舞台空间中。
值得肯定的是,除去爱欲带来的荒淫,唐·乔万尼的悲情一面也在终场中得到了较好的展现。终场中,面对石像的最后审判,唐·乔万尼顽强地说“不”,拒绝悔过,坚定的语气表达凸显出其与生俱来的自大,直至被火焰吞没,看起来像是一个无奈又决绝屈服的悲剧英雄。在正常演出中,我们可以看到,唐·乔万尼这个形象,不只是一个浪漫主义式的印象,更是一个愤世嫉俗的个人主义者,除了快乐别无所求,从一个闹剧人物形象转向了对生命本体的感悟。是爱欲,也是对禁欲主义以及世俗眼光的反叛与蔑视,是悲剧的抗争者。自此,爱欲与悲剧合为一体。
舞台的显像与隐喻
总体来说,此次演出除了细节上的一些改动,基本是较忠于原版的一次演绎。首先,精心设计并且制作的服装具有新古典艺术风格,给予洛可可式的精致装饰花边点缀,特别是唐·乔万尼的服装,红色斗篷披风尽显率性,以及同风格的道具摆设,配合上本就典雅的兰心大戏院的布置,这种用心的还原使观众瞬间代入至那个情境当中。
而在这种“复原”的大环境下,与之前上演的版本相对比,在这样一个舞台上以及演员们的表演中,我们可以看到新的构思所带来的显像与隐喻性。例如在第一幕最后一场中,音乐在此转入快板,催促着情绪在空气中发酵,众人异口同声地诅咒唐乔凡尼道:“这个恶棍,你的脑袋必遭天谴。” 这里情绪上的指责外化为具像的枪,为首的人使用它对准了唐乔凡尼,其余的人紧随其后,步步紧逼,与唐的恶行昭彰进行对立,舞台分立两边,这种显像的设计,一方面使观众明确为强烈的针对情绪的外化表现,另一方面属于教条性的教化隐喻。冲突和对立,分化与融合,通过舞台的显像进行表达。
又如终场,唐·乔万尼屋内。柔黄色光线舒缓着明朗的管弦乐,纯白色长条餐桌被覆盖上红色的浊旗。唐·乔万尼在用餐,仆人莱坡勒罗在一旁服侍着。和之前版本有所不同的是——他并不是独自用餐,数位身着白裙的女人头盖洁白蕾丝纱巾围绕餐桌而坐,她们仿若浸入空间的幻觉——去除言语,去除动作,与身下的椅子一样是无生命的、成为陷入环境中的一部分。这一新颖的设计如何去解读?或许为埃尔维拉内心一隅的隐喻,或许为即将而来的石像人的前锋预示,见仁见智。之后随着乐队紧缩的减七和弦的喧嚣,石像人宣判到来——这里也有独特的设计,简化了门的具象显现,观众看到的是,一个体积庞大的人,象一具统领生命的神,庄重而又威严地从餐桌上踏了出来,伴随着餐具残落的肃穆。随着音乐的冲突越来越剧烈,舞台浸入一片红色——仿若燃起的火焰,这种写实式的明切指向笼罩入一种宣判的神力感,使人堕入玄学的思考,最终唐在恐惧之下,堕入地狱。纵观,前部轻松活泼的音乐与悲剧和魔力的对立是忠于剧本的回归,而上述这些细节上独具尽心的考虑与改动,是舞台表现的显像与隐喻,催发成立了恶行本身的魅力的与罪恶的不可饶恕之间的冲突,这正是唐璜传奇的意蕴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