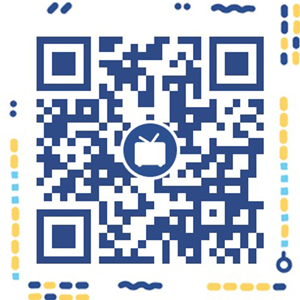又到了一年一度“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的时分,让我想起了那几首标志性的经典作品,想起了那几位令人尊崇的艺术家的脸庞,闵慧芬老师就是其中的一位。她从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上海之春”初创期走来,日益炉火纯青的二胡弓弦中流淌出来的一首首曲子如春风般地飘向四方,成为一段段经典。只是今年的“上海之春”前夕,我收到了一份缅怀闵慧芬老师座谈会的通知书,顿感唏嘘:闵慧芬老师已经永远告别了钟爱大半生的“上海之春”,她的琴弦彻底断了。
人去魂在,弦断音存。我看着这份通知书,感怀、感佩这位艺术大家的件件乐坛往事一一浮现,其中有十余年前的“初一北飞”。
那是2004年大年初一的中午,当人们都在共迎佳节、团聚开怀之时,我已置身于万米高空的航班,向北飞去。环顾机舱四周,人并不多。随我齐飞的有我的制作团队,还有几位艺术家,闵慧芬老师就是其中的一位。我们共同的任务是在两天后的法国巴黎上演一台“2004年中国文化之夜”大型音乐会,地点在著名的凡尔赛宫皇家歌剧院。航程足足飞了12个小时,加上遭遇巴黎少见的暴风雪而迫降异地机场,又花去了5个小时。这漫长的17个小时的机舱生活对我来说还能适应,但对我的邻座闵慧芬老师来说,却出乎意料的苦涩。闵慧芬老师一上飞机,便不停地研究着曲谱,还谈兴浓浓地向我们介绍着将要在凡尔赛宫皇家歌剧院演奏的二胡作品——中国陕北的《迷糊调》的艺术风格和历史沿革,绘声绘色,认真劲像老师上课一般。但是,数小时后,飞机开始了剧烈的颠簸,闵慧芬老师一下子陷入了头晕眼花、脸色发白的“怪圈”,并开始呕吐起来。我知道她曾患过重病,是和死神殊死搏斗过的,体质较弱。我马上请来乘务员帮助把座位大角度的调整好,让闵慧芬老师斜躺休息。此时,闵慧芬老师声音很弱地说:“这是晕机,是我的老毛病,长途飞行更容易犯,只要让我平躺就会好。”“被观众赞美、推崇的艺术家是幸福的,但又有多少人知晓其艰辛的付出呢。”看着紧闭双眼、默默坚持的闵慧芬老师的神情,一路陪伴、一路见证的我,内心充盈着感慨和敬意。
当飞机飞临巴黎上空时,开始恢复精神、重新坐起来的闵慧芬老师对我说:今年春节本来早有安排,但一接到法国总统希拉克夫人真诚的演出邀请时,我很激动。因为凡尔赛宫的演出是2月3日,这恰巧是18年前我与死神搏斗,开刀动手术的难忘日子,实在是太巧了。当时我唯一的希望是无论如何要活下来,没想到一转眼,已经有质量地活了18年。所以,尽管是过年期间,我放弃全家团聚的机会也要出发,我要用琴声传递中国艺术的美妙,用琴声赞美可爱的生活、可爱的生命。
到了凡尔赛宫排练现场,闵慧芬老师两眼放光,神采奕奕、气度非凡。她独奏的中国陕西民歌《迷糊调》由法国国家交响乐团担任协奏。但是,一个小时排练下来,法方指挥和乐队还是达不到闵慧芬老师的标准要求。于是,她索性和法国指挥家沟通并征得同意后,现场当起了指挥,对全曲的各个关键段落边比划边讲解起来,场上的法国同行们迅速开窍,整个排练有效推进。当晚正式演出中,当希拉克夫人亲自走上舞台,向全场观众介绍专程从中国请来的二胡演奏家闵慧芬出场时,全场掌声雷动。法国交响乐团的乐手们真诚地表达了对排练时当过他们“客席指挥”的中国二胡演奏家的敬意……
春暖花开的“上海之春”时节,再一次想到了“闵慧芬老师初一北飞”故事,这里面有“高峰之作”的必有路径;有艺术大家的成功天梯,有“上海之春”新人新作学习的方方面面。
滕俊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