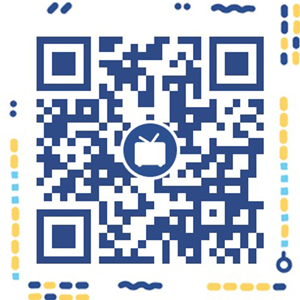西贝柳斯音乐节演出现场
2015年是芬兰作曲家让·西贝柳斯诞辰150周年,或许也是最为人熟知的作曲家“大年”,古典乐界干脆将今年称为“西贝柳斯年”。从去年下半年开始,西贝柳斯最出名、最常上演的几部作品,便频繁出现在各音乐会节目单上。5月12日至14日,来自芬兰的拉蒂交响乐团在指挥奥科·卡姆带领下,于上海大剧院连演了七部交响曲,完成了西贝柳斯壮阔的上海之行。
最后一场音乐会前,我曾与芬兰驻沪总领事龙玛丽女士交谈。她眼中的芬兰植被丰富、湖泊众多、人口稀少,是享受安宁的好去处。我好奇这个国度喜欢什么样的音乐,她告诉我,当代芬兰人什么音乐都能接受,重金属音乐的繁荣更是驰名世界。然而即便时过境迁,未必所有人都听过西贝柳斯的作品,但他的名字在这个“千湖之国”依然妇孺皆知。
当晚的音乐会以《第三交响曲》、《第五交响曲》、《d小调小提琴协奏曲》为西贝柳斯音乐节作结。从第一个音符开始,西贝柳斯就构建了一幅北欧风光和北欧人民精神世界的蓝图:极少的音乐元素,一个主题的反复出现、变形,有规则地打碎、整合、再拆分,通过不同声部来表现,就像透明无色的冰雪世界,无数呈规则图形的雪花、冰晶在空中此起彼伏。当《第三交响曲》奏响颂歌一般的终曲,四散的雪子瞬间铸成广袤的冰原。
第一次欣赏西贝柳斯交响曲的朋友说,听西贝柳斯就像在大海中航行,风平浪静,没有波折。这种感受很直接。西贝柳斯的音乐确实十分有规制、发展脉络也很稳健。很难想象,在他的同时代,马勒、斯特拉文斯基、勋伯格等人的作品极尽夸张之能事,他却继承了浪漫主义传统的创作路径;从演出阵容来看,他的乐团参演人数也和前辈勃拉姆斯一样精炼,打击乐器有时只用一台定音鼓,连镲都不用。
史料记载,西贝柳斯1907年曾与马勒有过一次交谈,两人互换了对交响曲创作意义的看法。西贝柳斯认为交响曲最重要的是“深刻的逻辑和内在联系”,相反,马勒认为交响曲应该是“整个世界”,创作交响曲就是要“包罗万象”。因循这个思路,马勒创作了《第八“千人”交响曲》,企图用夸张的音响塞满整个音乐厅。
相比之下,西贝柳斯是个另类的“叛逆者”。他继续着严谨创作,不断回望柴可夫斯基、鲍罗丁等俄罗斯作曲家的传统,以获得新的动力(另一个典型的例子可能是拉赫玛尼诺夫)。当后辈不断打破陈规,音乐厅里的老观众被吓唬得一愣一愣时,以《芬兰颂》发出民族独立呐喊的民族英雄西贝柳斯,笔法却越来越简练——《第五交响曲》的第一乐章犹如电影慢镜头中的巨大瀑布,白练般缓缓从悬崖降下。
和西贝柳斯类似,拉蒂交响乐团亦特立独行。媒体评价其为“小镇的奇迹”,意在赞叹一个不怎么有古典音乐传统的国度,何以在当代培养出如此多活跃的指挥和乐团。当年奥斯莫·万斯卡带领这支乐团走向世界,除了积累西贝柳斯全套曲目,他们在唱片工业的贡献也很大,多数乐迷通过BIS厂牌出版的成套录音认识了他们,而能说服大家走进剧场接连欣赏三天大戏的,也只有他们。
三天音乐会,乐团整体呈现出越战越勇的态势。最后一晚,乐团弦乐华丽,音色厚重绵密,管乐则有些“不走寻常路”,坚硬嘹亮、直来直去的声音好似冰制刀锋直插耳朵,和我们常听的德奥乐团多有不同。
指挥家奥科·卡姆是个和善的长者,拍点丰富,没有过多的表达要求。担任《d小调小提琴协奏曲》小提琴独奏的伊利亚·葛林戈茨,音色甜美,演奏干净。他的演绎十分遵循乐谱,也没有夸张的表情,倒是和乐团的声音形象一致:没有溢出的情感,没有外向的激情,或许他们的情感也像西贝柳斯一样,隐藏在冰冷的外在世界之后。
当年西贝柳斯和马勒的争论看似无解,一个世纪之后的我们已经给出了答案。更多观众热爱音响效果丰富、情感夸张、神经质的马勒,或许因为他从来都将作品指向未来,而“怀旧”的西贝柳斯只有在纪念年才有机会一展风采。在他的音乐中,我们听到更多的是一种情怀——那种身处繁忙大都市,却一心向往内心安宁的欲望。
奥斯莫·万斯卡曾在专访中告诉我,他在芬兰时,最喜在森林和湖泊旁长时间漫步,在那里他遇不上一个人,只有大自然和心灵对话。故乡于他而言就是千踪尽灭,万籁俱寂。那是芬兰最好的声音。只可惜芬兰人的寂静日常,却只能是身处“魔都”的我们的一种长久奢望。
特约刊登
顾超